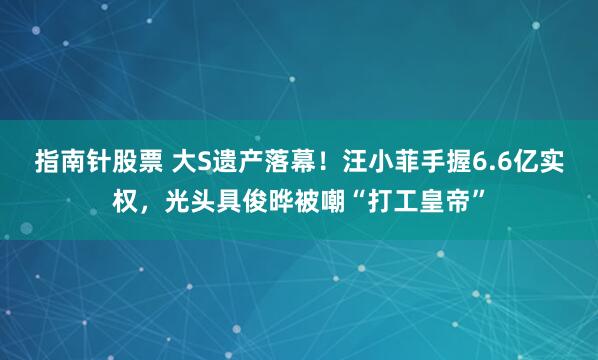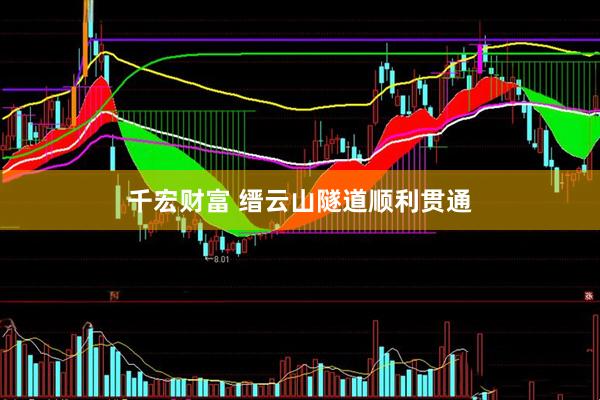日前,中山大学陈斯鹏教授编著的《新见金文字编(2000—2019)》正式出版。作为2012年初版的增订本,这本耗时多年增订的著作公牛配资,不仅把21世纪前20年新发现的金文“一网打尽”——仅2010到2019年的新出金文就有2500件左右,更像一把“钥匙”,解开了不少困扰学界多年的古文字谜题,为研究商周青铜铭文提供了更全面、更精准的参考。
诞生与升级:从课堂需求到“十年之约”
这本书的缘起,要从2007年陈斯鹏教授的一堂课说起。当时他在中山大学主讲“青铜器铭文研究”,发现学生们常用的参考资料——容庚先生的《金文编》及后续校补著作,跟不上21世纪以来新出土的金文节奏。“很多新发现的青铜器铭文,在旧书里查不到,研究起来特别不方便。”于是,他萌生了编一本“新金文字典”的想法。
2012年,《新见金文字编》初版问世,立刻成了古文字研究者的“手边书”:每个字下面都标注着出自哪件青铜器、属于哪个时代、原文里怎么用,还附上陈教授对疑难字的考证分析。但书刚编完,陈斯鹏就埋下了一个“十年之约”:“金文资料更新太快,估计每十年就得大改一次,才能跟上研究进度。”
没想到这个预判很快应验——2010到2019年,新出金文的数量比前十年还多,光没见过的“新字”就多了不少,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。“要是不及时整理,这些新发现就没法被更多人用上。”从定下增订计划到最终出版,陈斯鹏教授和团队又花了数年,把书的体量几乎翻了倍:总字数从77万字增至150万字,正编收录的单字从1425个增至2230个,新增的817个字头里,436个是此前金文中从未出现过的“新字”;就连暂时认不出的“待释字”,也从83个补充到205个,尽可能网罗了前20年的新资料。
啃下“硬骨头”:认生字、改错误、筛资料
增订过程远比初版更难,陈斯鹏把最棘手的挑战总结为三块“硬骨头”,其中最耗心力的就是“认生字”——疑难字考释。
“写论文可以只挑自己有把握的问题说,但编字编不行,每个字都得有说法,不能绕着走。”陈斯鹏说,新增的2500件金文里,藏着不少长得奇怪的字,有的连前辈学者都没定论。学生们能帮忙整理资料,但核心的释字环节,只能他自己“死磕”:为了一个字,要翻遍几十本古籍和研究文献,对比不同时期的金文写法,梳理出能说服人的证据链。“快的话几天能有眉目,慢的话卡几个月,甚至几年都有可能,这也是书稿改了又改、一再延后的原因。”
除了认生字,订正初版的错误也很关键。比如初版附录中“ ”形字,过去学者猜它是“环”“雍”“吕”等十几种说法,都没实锤,只能归到“待释字”里。这次增订时,新发现的金文“豫”字帮了大忙——“豫”的左半边正是这个神秘字形。“‘豫’以它为声旁,一下子就确定了,它其实是‘予’字。”陈斯鹏说,这个突破不仅让“予”字有了明确归属,还能帮着解读更多和“予”相关的古文字、古文献,用处不小。
”形字,过去学者猜它是“环”“雍”“吕”等十几种说法,都没实锤,只能归到“待释字”里。这次增订时,新发现的金文“豫”字帮了大忙——“豫”的左半边正是这个神秘字形。“‘豫’以它为声旁,一下子就确定了,它其实是‘予’字。”陈斯鹏说,这个突破不仅让“予”字有了明确归属,还能帮着解读更多和“予”相关的古文字、古文献,用处不小。
还有些初版误收的“问题铭文”也被清理出去。“有些青铜器不是科学发掘的,上面的铭文可能是假的。”陈斯鹏解释,这次增订时,他们逐一核查资料,把初版里几件存疑的铭文删掉公牛配资,“这对于确保资料的可靠性至关重要。”
至于资料筛选,陈斯鹏教授有个简单的标准:没见过的新字、写法特别的字,一律收录;早就认识的字,就挑能体现时代变化、用法特别的例子——比如同一个字在西周、春秋、战国的不同写法,这样读者能清楚地看到文字的演变过程。“所有资料均来自公开发表的书刊,力求全面反映金文形体与用法的演变。”
解“文字谜”:从青铜器名到“达殷”释义
这本增订本不光是“资料集”,还解决了不少学界争论已久的“文字谜”。
比如金文中器物名称前常出现一个以“鼎”“爿”(或从“肉”从“刀”)为核心构件的修饰语。过去有人说它是“将”,有人说它是“肆”(古代祭祀时解牲的仪式),但“肆”只能和食器有关,无法解释其修饰酒器、水器的用法。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。”陈斯鹏说,这次增订时,新发现的几件金文帮了忙:曾仲姬壶上,有个“从爿从酉”的字修饰“壶”;景之朝鼎上,“从爿从酉从止”的字修饰“彝”;还有夆子詹的簠和壶,用“从爿从言”的字来修饰。“这些字都带‘爿’,又都用来修饰器物名,肯定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。”结合古人“从爿”的字常读“将”的习惯,陈斯鹏确定这个字该读“将”,表示“将享已故之人”,意思是“用来祭祀已故之人的器物”,这下不管修饰什么器型都说得通了。
就连“达”“谏”这种看似常见的字,增订本也挖出了新解读。比如金文里常出现“达殷”,过去有人说“达”是“通”,有人说读“挞”,但新发现的曾侯与钟上有“达殷之命”,“通命”讲不通,“命”为抽象概念也不可“挞”。“有学者推测‘达’可能是‘替代’的意思,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”陈斯鹏进一步查证,发现《说文解字》里“达”和“迭”(迭代、更替)可以互通,“所以‘达殷’其实是‘迭殷’,指更替殷商的天命,这样就顺理成章了。”
还有“谏”字,近年有人说该改释为“敕”,但陈斯鹏不认同:“‘谏’是‘言’字旁加‘柬’,字形很明确;而且清华简里和‘谏’对应的是‘柬’,‘柬’根本没法读成‘敕’。”他研究发现,“谏”在金文中有“治理”的意思,还能用于诉讼场景,比如“谏訊有粦(譖)”,结合“柬”和“簡”(简)常通用的规律,他推测这里“谏”可读“简”,意思是“核验”,和《尚书·吕刑》里“五辞简孚”(用五种供词核验实情)的“简”正好呼应。
陈斯鹏教授对南都记者表示,作为涵盖21世纪前20年新见金文的总结性著作,《新见金文字编(2000—2019)》不仅聚焦金文本身,还结合清华简、安大简等楚简研究成果,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前沿性。“《新见金文字编》的增订工作永不会止步。”他说,“新书刚出,材料已滞后数年,新一轮增订即将启动。”
面对面——
陈斯鹏:编字编像“扫雷”,每一个疑难字都是待解的谜题
南都:您提到疑难字考释耗时久,有没有哪个字的解决过程让您印象特别深?
陈斯鹏:“予”字吧。初版时,甲骨文、金文中那个“ ”形字有“环”“予”“雍”“蛤”“吕”“宫”等十几种说法,以“雍”“环”二说影响最大,但其实都缺乏直接证据,所以初版时,我把它当作存疑字放在附录。增订时看到新出金文里的“豫”字,左旁就是这个形,可以证它就是“予”字,所以这次增订本就把它调入正编了。“予”字在古文字资料中牵涉甚广,它的释出对于“予”字本身的历史源流、相关字的结构分析,以及相关文本的理解,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不过,这还没完,我在按语中提出一个初步意见,怀疑“予”字本象房舍勾连之形,为“序”和“舍”之共同初文。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论证。这种从存疑到确证,再到深挖本义的过程,就是考释的魅力,也最耗精力。
”形字有“环”“予”“雍”“蛤”“吕”“宫”等十几种说法,以“雍”“环”二说影响最大,但其实都缺乏直接证据,所以初版时,我把它当作存疑字放在附录。增订时看到新出金文里的“豫”字,左旁就是这个形,可以证它就是“予”字,所以这次增订本就把它调入正编了。“予”字在古文字资料中牵涉甚广,它的释出对于“予”字本身的历史源流、相关字的结构分析,以及相关文本的理解,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不过,这还没完,我在按语中提出一个初步意见,怀疑“予”字本象房舍勾连之形,为“序”和“舍”之共同初文。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论证。这种从存疑到确证,再到深挖本义的过程,就是考释的魅力,也最耗精力。
南都:近年来,古文字研究领域有哪些新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话题?《新见金文字编(2000—2019)》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下,处于怎样的位置,又将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 ?
陈斯鹏:古文字领域的研究热点,往往与重要新材料的出土紧密关联。最近二三十年,热度最高的当数战国楚简研究——尤其是清华简、安大简等一批珍贵简牍公布后,一直是学界关注的核心。目前还有好几批新出的重要楚简资料待公布,未来必然会掀起新的研究热潮。
相比楚简,新见金文的研究热度虽稍逊一筹,但也是当前学界关注度较高的领域。《新见金文字编(2000—2019)》在新见金文研究里,算是具有全局性和总结性的核心著作:它不局限于金文本身,还会结合楚简研究等最新成果来破解金文释读难题,既有开放性,又能紧跟前沿。相信这本书能为古文字学的整体发展提供积极助力。
南都:在数字化时代,古文字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。您认为新技术(如数据库、人工智能等)对古文字研究有哪些影响?
陈斯鹏:不可否认,电子化资料和专业数据库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多便利,能大幅提高工作效率。在技术应用上,我们确实得积极学习、与时俱进。这次增订《新见金文字编》时,我就有很切实的体会——因为处理金文图片时沿用了10多年前的旧方法,导致不少图片进入排版系统后精度不足,影响了呈现效果。后续工作里,我肯定要学习新的技术手段,把这个问题解决好。
不过,我们也得客观看待数字技术的开发难度和实际效益。比如古文字相关的专业数据库,很多机构都尝试过或正在做,但最终能正式完成、还能推广使用的,其实非常少见。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,这类数据库对人力、财力、时间的投入要求极高,实际投入往往难以匹配需求。至于现在各行业都在谈的人工智能,要把它用到古文字研究里,理论上是可行的,但前提是得有极其巨大的资源投入。目前,我对这一点暂时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。
采写:南都记者 周佩文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公牛配资
实盘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